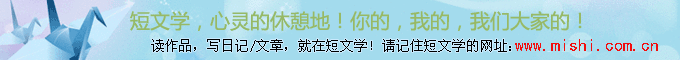十分爱七分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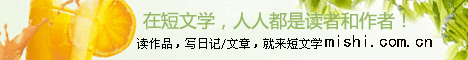
我平生第一次掌心的热和是她送给我的。
那一年,父亲猝逝,母亲一夜之间几乎白了头,不停地啼哭,问我,从今以后,咱们可怎么办呢?
父亲在我的心里就是神,无所不能是我经常用来形容他的词。
父亲寡言少语,可说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然而如同能医者不能自医一样,正当盛年却死于非力。
他死了,家里面的顶梁柱也就塌了。
追悼会上,母亲被亲戚朋友扶持着哭得死往活来,我却看着父亲的遗像恍如隔世。
邻居们全挤在了狭窄的巷子里看热闹,小声地议论着周家穷了,败了,啧啧地咂着舌头,眼睛里满是欢喜与好奇,探头探脑地窥视着,生怕遗漏一点点的新闻。村里的人大多是和父亲要好的,可现在,我的家散了,在他们的眼里,却看不到一丁点儿同情或温情,有的只是幸灾乐祸。
我恨恨地攥紧了拳头,更是恨恨地和那些躲躲闪闪的眼神对视,逼着他们扭过头,退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父亲死了,我哭泣了,眼泪一滴又一滴地落在了他的坟前,是无以言喻的落寞与尽看。
直到这一刻,我才真切地意识到,父亲死了,我的世界也就改变了。
所谓死,就是意味着消亡,意味着尽裂,意味着没有,意味着虚无,意味着彻头彻尾地改变。
那一年,我上初三。
如花的花季就在那么一场大张旗鼓的葬礼中给劫杀了,一切童年的幻想都那么不可思议地结束了,沉淀了,也腐烂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恐慌的,我几乎已不习惯和以前的好友们相处,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我感受到了我内心孤独的强大。
所以,我想逃,逃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那一年玄月,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县城里最好高中的校大门。
万事皆空的坦然和视死如回的豁达让我在陌生的环境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我已经忘记了与她怎么相识的了,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和她在一起的快乐,从来没有过的快乐。
我甚至渴看能够天天和她在一起
我想那就是喜欢吧。
可我却不敢说出口。
我喜欢你,她说。
我始料不及以至措手不及。
我带你往看我爸爸吧,我想他会喜欢你的。
她兴高采烈,我心如刀绞。
在满是青冢的山坡上,她忽然用她小巧的左手把我暴露在空气中早已冰冷的右手牢牢地扣在了一起,热和在刹那间充斥着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我本能地也紧了紧我的手指头,生怕会忽然间失往这份热和一样。
她说,爸爸固然死了,可是生命仍然要继续往前走,你要快快地长大,扶持妈妈,让自己,也让四周的人都快乐起来,明白吗?
我不明白,但我记得很深,视之为生命格言。
父亲的死,使我在驟然间失往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依靠,于是我视她为唯一救命稻草。
内心深处,由于父亲的猝然往世而撕开的一方残漏,因她的温言软语而静静地得到缝补。
那一年,我上高一。
十七岁,传说中的雨季。
女娲补天的故事在我与她之间凄美地上演,可是精卫填海地悲剧却从此静静地埋下了序幕。
复读一年后,我奇迹般考上了大学。
固然不是我喜欢的学校,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要离开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