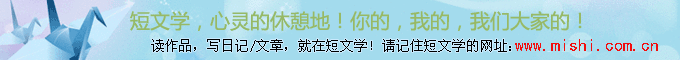天祭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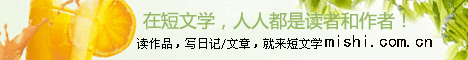
童年的梦,是前世一些残存的记忆,它逐渐被淡忘,刷新刷白,然后涂上新的颜色,接受今世新的记忆。——题记
玄月九,重阳。一个悲壮的日子,我悲壮地出至。“哇……”地一声,惊天地,泣鬼神。
娘给我取名叫天祭。她告诉我,九是一个命数,它代表着循环,你地出生,是对前世未完地记忆。说地时候,母亲一脸严厉,像一个得道高僧。不!应该叫得道高尼。
小时候经常做一个梦,梦里雪花纷飞,刀光剑影。有一个人,漂亮如同雪中飘飞的蝴蝶。快乐地在飞舞。然后她嘴角忽然溢出了血,双手怀抱自己,瑟瑟发抖。看到这,我莫名地悲伤,想走过往抱紧她,却又无法靠近。她地脸一直模糊。
她慢慢站起身,低着头漠然前行。风吹过,像哭泣地声音。
我有个妹妹叫冼盏。眼睛干净透彻,却透着死亡般的忧韵,给人一种灾难般的感觉。从小我们就住在山上,很高的山,娘从没让我们出过远门,只是天天早晨让我们出往打柴,中午的时候回来。我和妹妹从没见过一个人,除了母亲和对方,由于高山上,几乎没什么人。
有时候,能听到对面山头上,幽幽地传来歌声。母亲告诉我,他们事一些采药或打猎的人。妹妹问我,哥,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那些人呢,他们长什么样呢?
我笑着抚摩她得头发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从小对人有着各种幻想,向往山下的那些在母亲口中的尘世。
该来的还是要来,不该来的也来了。
在我19岁那年,母亲忽然消失,只留下一封信和一管萧。信里告诉我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事和一些希奇的事。
她说,实在我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她是在山下一条小溪旁捡到的我,旁边还有一管萧和一封信。信上说叫我拿着这管萧往找一个人。然后就没什么别的话了。
我真为母亲感到可惜,由于她真是一个糊涂的人,竟然忘了写妹妹冼盏是不是她亲生的,还是一样也是被捡回来的,而且还不给我们留个包袱,放些银子什么的!
我想她真是个尽情的人,母亲抛下我们走了一点也不难过,同时也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每当我问起我们的父亲是谁时,她总是像我一样摸着妹妹头发那样摸着我,笑着回答,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当时我就纳闷了,怎么像在讲童话故事啊?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妹妹下山了。我看见她提着一个包袱,便问她,你拿了什么呀?
她说,衣服呀。我“哦”了一声,看着她活蹦乱跳的样子,自己也觉得兴奋,她只比我小个把月,身材已凹凸有致,活像个人样。
切,什么逻辑,她本来就是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希奇,就问她,冼盏,娘走了怎么没见你伤心呀?
她拽着我胳膊说,由于还有哥哥你陪着我呀。
那你怕不怕被坏人欺侮?
不怕,有你保护我呢,我怕个啥!
那你知不知道我怕不怕?
她看了我半天,然后很严厉地说,不怕,由于有我保护你呢。
然后我们就一起笑了,笑声和着夕阳在山间回荡。
我和冼盏来到一个叫“远”的小镇,光听名字,就觉得挺飘逸,而远不可及的,可它就在我们眼前,那叫一个字:牛!
可名字不能当饭吃,饭?然后就觉得肚子一个劲儿地闹革命,刚想开口,却闻声妹妹说,哥,我饿了。